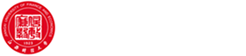记得有一年,父亲带着读小学的我回湖北老家过年,然后返回瑞昌。腊月二十九下午三点多,当我们从武穴坐轮渡回到码头,却发现已经没有回瑞昌的班车了(那时的班车本来就少,过年时就更少了)。父亲苦笑着,对我说:没有车了,我们只能走回瑞昌了!我几乎要哭出来了:走回去?有多远啊?父亲回答:也不是很远,二十多里吧!(其实有三十五、六里)我毫无办法,只好哭丧着脸、嘟着小嘴展开自己人生的第一次"徒步"旅程:前面还有二十多里路,让我这个小屁孩情何以堪!万般无奈,我只能叹叹气、咬咬牙,迈开小腿,跟着挑着行旅的父亲蹭蹭而行!这样,走出了三、四里路后,我这个小屁孩已经疲惫不堪,两条小腿像绑了两个沙袋一样!但是,看着空无一车、一人并通向"无尽"远处的公路,我那颗小小的心还在下沉:天啊!还有多远啊?我们天黑前能走回瑞昌吗?
忽然,一辆绿色"豪"车(北京吉普)飞驰而至,嘎然而止:原来是父亲的熟人!我和父亲大喜:垮上"豪"车,爽也!"豪"车就是非同一般:风驰电掣地就到了瑞昌——我还没坐过瘾呢!在回家的路上,父亲还对我说:你真是懒人有懒福,每次碰到要走路时都可以遇到熟人的车!(前面也有过两次这样的"奇遇")当时,我很有点小得意:小懒人也许真的有点福气哦。现在,我才忽然发现:已在天堂的父亲对儿子的爱原来可以这样表达的啊!
1985年,我考上了江西师范大学。父亲的最好朋友李叔叔(当时是县里汽车修配厂厂长)特意安排了一辆"专车"送我到南昌读书:当时,正好有一辆吉普车要到南昌蒙上顶棚。于是,父亲母亲就带上为我准备的各种"装备",和我一起坐上无"顶"的吉普车,驶向我人生的第一所大学。
炎炎烈日下近五个小时的车程并不痛苦:前往大学的兴奋,加上父母的陪伴——我觉得阳光是明媚的,风儿是柔和的!
到了师大的宿舍,我们发现一个不大的寝室要睡6个人:3张看上去"年龄"不小的木床(上下铺),稍微用力一摇就会吱吱嘎嘎地响起来!母亲一看,就伤心了:这个破床能睡吗?孩子,我们回家去吧——不读这个大学了。父亲马上冲母亲一瞪眼:不要胡说!那么多大学生都读出来了——也没听说谁从床上掉下来了!安顿好了以后,父亲就拉着母亲走。母亲走着、走着忍不住回头,我看见父亲没有回头,而是侧着脸在和母亲说着什么:不要老回头,免得让儿子不好受。
大四时,我得了急性肝炎:住进了南昌传染病医院。父亲得知后马上赶到南昌,来照顾、陪伴我。他的脾气一下子好了很多:每天一大早就从师大(他睡我的床)买好早点赶到医院,然后忙这忙那,还一个劲地好言安慰我。在父亲的精心照顾下(不可否认医生护士的认真治疗),我很快康复出院了。
大学毕业,我被分配到江西省机械厅下属的方向机厂:那是一个只有100多人的一个小厂,围墙后面就是梅岭——晚上"狐狸精"(蒲松龄先生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女主角)会不会从后面的山上爬进来呢?我当时的心情极其沮丧:这是发配沧州啊!陪着我的父亲安慰我:这里环境挺好的,这么多树——夏天多凉快!(后来,我到南昌齿轮厂子弟学校任初中化学老师)1990年,第一次失恋的我非常痛苦、消沉:觉得人生就是灰色的!这时,父亲的一声断喝打醒了我:你就这么没出息!你是个男人?
我在南齿工作的三年(人生最低沉的三年),父亲多次从瑞昌坐长途汽车来看我:带来吃的和一壶(10斤)煤油(那时的煤油要靠一些关系才能买到)。这样,我就可以用那个小小的煤油炉子做点菜了。而当我送父亲走的时候,我才发现父亲已经渐渐地老了:就像朱自清先生在《背影》中描写的父亲那样!
1997年,我考上了武汉大学的博士研究生。父亲和母亲一起,又一次把我送到了武汉大学。
1999年,江财分给我一套大的集资房,但我没有钱。父亲,腰上缠着父母全部的积蓄,坐火车到南昌:将3万2千元递到我手上!
记不得哪一年的一天晚上,我突然接到经济学院黄老师的一个电话:张博导,我现在和你父亲在一起!我当时万分惊讶:怎么回事?原来,黄老师到瑞昌做一个课题的调查:在柳湖边介绍自己是江西财大经济学院的老师,并给湖边的一些老人发问卷。父亲就对黄老师说:我儿子也在财大工作,不知道你认不认识?黄老师问:你儿子叫什么名字?在父亲告诉了我的名字后,黄老师说:你儿子在财大很厉害的,早就是博导了。虽然我不在现场,但我知道,在周围那些老人羡慕的眼光中,父亲一定非常的开心:他为自己的儿子感到自豪和骄傲!
2009年暑假,我带着女儿回家小住。父亲非常开心:竟然翻出几十年都没有用的弄小虾的工具——带女儿和我去柳湖弄小虾。湖边的工作人员过来赶我们:这里不准弄鱼。父亲给他递上一根烟,说:我这个东西又弄不了鱼,只是带孙女来弄点虾米玩一下——她难得回来。看着女儿兴奋、高兴的样子,父亲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可是,谁会想到,几天以后,父亲就在这柳湖边猝然倒下: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十年生死两茫茫,每念父亲儿断肠。安息吧,父亲!(文/张进铭 编辑/邱朝聪)